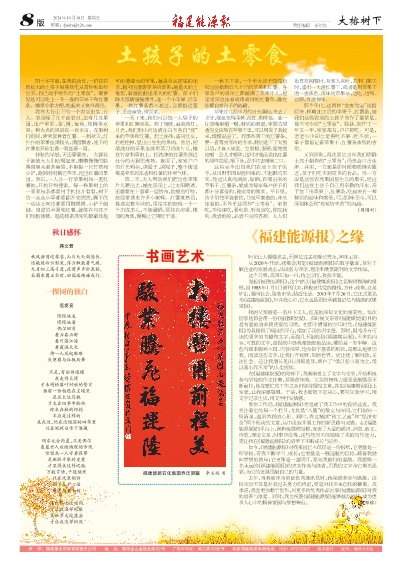发布日期:
土孩子的土零食
文章字数:1,527
四十多年前,在我的故乡,一群在农场长大的土孩子最喜欢吃从青纱帐里捡回来,自己动手制作的“土零食”。最常见是可以吃上一冬一春的苹果干和红薯条。携带非常方便,吃起来又格外香甜。
我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农场出生、长大。农场除了几千亩农田,还有几处果园,出产苹果、梨、桃、葡萄、核桃等水果。稍大点的果园有一百多亩。在果树行距间,常常套种着红薯。一到秋天,红扑扑的苹果挂满枝头,满园飘香,地下的红薯也开始生得一窝连着一窝。
仲秋的早晨,天还蒙蒙亮,一大群孩子就被大人们吆喝起来,懵懵懂懂的胳膊窝里夹着条麻袋,手里提一只竹篮和小铲,跑到刚刚摘完苹果、挖出红薯的果园。然后,一人分一行苹果树和一垄红薯地,开始仔细搜索。每一株果树上的一束束枝条都要用手扒拉开看看,树下的一丛丛小草都要翻开来瞧瞧,脚下的一块块土坷垃都要用脚踢踢、小铲子刨刨。遗留的苹果和红薯,就像在与孩子们玩捉迷藏。越是枝条茂密的隐蔽处越可能遗漏大的苹果,越是草丛密集的地方,越可能遗落更多的苹果;越是大的土堆里,就越能翻出来大的红薯。孩子们睁大眼睛慢慢搜寻,连一个小苹果、烂苹果,一块红薯条都不放过,全要拾进篮子、丢进麻袋,带回家。
一天下来,我们可以拖一大袋子的苹果和红薯回来。到了傍晚,就着路灯、月光,我们到小河边清洗白天各自“搜”来的苹果和红薯。泥土洗净,露出红皮,烂疤挖掉,显出白生生的果肉。然后,把清洗好的苹果全部用菜刀切成片儿,摊在竹席和草帘上。把洗净的红薯条倒进灶台的大锅里煮熟。夜深了,家家户户仍灯光明亮,满屋子、满院子,整个街道都是苹果的浓香和红薯的甘甜气味。
第二天,大人帮助我们把这些苹果片儿晒出去,铺在房顶上,让太阳晒透。还需要在上面罩一层纱布,防蝇虫叮咬,却经常诱来许多小蜜蜂。红薯煮熟后,挑选完整形状的,用结实的细线一个一个串成串儿,不能暴晒,要挂在房梁、楼顶的角落,慢慢让它阴晾干透。
一秋天下来,一个半大孩子轻轻松松也能拾到百八十斤的苹果和红薯。各家各户的房顶上都铺满了苹果片儿,屋里梁顶也挂着成串成排的红薯条,像在炫耀自家孩子的能耐。
苹果片儿经半月的日头暴晒,失去了水分,颜色变得深黄、淡红、咖啡色。拿一片放嘴里嚼一嚼,特别的筋道,苹果的甜香完全浓缩在苹果干里,可以用袋子装起来,慢慢品尝了。而那些阴干的红薯条,要一直等到寒冷的冬季,特别是下了大雪以后,才真正成型。它很韧、很硬,要使劲地嚼一会儿才嚼碎,这时才能品尝出红薯的异样甘甜,咽下肚,忍不住去啃第二口。
这些完全出自我们农场土孩子的手,从田野果园里捡回来的、不起眼的果实,经过认真的清洗、晾晒,自制出来的苹果干、红薯条,就成为每家每户孩子们都十分喜爱的、最家常的零食。平日里,孩子们兜里装着的,书包里塞着的,床头挂着的,不外乎这两种“土零食”。家里吃,学校里吃,看电影、听戏也吃,你吃我的、我尝他的,品尝不完的香甜。大人们也喜欢闲暇时、有客人来时、去串门聊天时,盛出一大盘红薯干,或者是用苹果干泡一壶浓色、浓味的苹果茶,边吃、边喝、边聊,有滋有味。
那个年代,这两样“变废为宝”捡拾回来、粗略加工后的苹果干、红薯条,被我们这些农场的土孩子当作了最常见、最不可少的“土零食”。收获、制作了一年又一年,家家都有,户户都吃。可是,老老少少却总觉得吃不够、吃不烦,一辈子都惦记着苹果干、红薯条浓缩的香甜。
又到深秋,再次回忆当年我们那群土孩子制作的“土零食”,仍然会口舌生津。其实,一方面是那时候物质确实匮乏,孩子们吃不到更多的食品。另一方面是这些农场果园里生长的果实,经过我们这些土孩子自己用辛勤的汗水、亲手加工出苹果干、红薯条,吃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滋味和感受,可以回味至今,可以深刻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周国利)
我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农场出生、长大。农场除了几千亩农田,还有几处果园,出产苹果、梨、桃、葡萄、核桃等水果。稍大点的果园有一百多亩。在果树行距间,常常套种着红薯。一到秋天,红扑扑的苹果挂满枝头,满园飘香,地下的红薯也开始生得一窝连着一窝。
仲秋的早晨,天还蒙蒙亮,一大群孩子就被大人们吆喝起来,懵懵懂懂的胳膊窝里夹着条麻袋,手里提一只竹篮和小铲,跑到刚刚摘完苹果、挖出红薯的果园。然后,一人分一行苹果树和一垄红薯地,开始仔细搜索。每一株果树上的一束束枝条都要用手扒拉开看看,树下的一丛丛小草都要翻开来瞧瞧,脚下的一块块土坷垃都要用脚踢踢、小铲子刨刨。遗留的苹果和红薯,就像在与孩子们玩捉迷藏。越是枝条茂密的隐蔽处越可能遗漏大的苹果,越是草丛密集的地方,越可能遗落更多的苹果;越是大的土堆里,就越能翻出来大的红薯。孩子们睁大眼睛慢慢搜寻,连一个小苹果、烂苹果,一块红薯条都不放过,全要拾进篮子、丢进麻袋,带回家。
一天下来,我们可以拖一大袋子的苹果和红薯回来。到了傍晚,就着路灯、月光,我们到小河边清洗白天各自“搜”来的苹果和红薯。泥土洗净,露出红皮,烂疤挖掉,显出白生生的果肉。然后,把清洗好的苹果全部用菜刀切成片儿,摊在竹席和草帘上。把洗净的红薯条倒进灶台的大锅里煮熟。夜深了,家家户户仍灯光明亮,满屋子、满院子,整个街道都是苹果的浓香和红薯的甘甜气味。
第二天,大人帮助我们把这些苹果片儿晒出去,铺在房顶上,让太阳晒透。还需要在上面罩一层纱布,防蝇虫叮咬,却经常诱来许多小蜜蜂。红薯煮熟后,挑选完整形状的,用结实的细线一个一个串成串儿,不能暴晒,要挂在房梁、楼顶的角落,慢慢让它阴晾干透。
一秋天下来,一个半大孩子轻轻松松也能拾到百八十斤的苹果和红薯。各家各户的房顶上都铺满了苹果片儿,屋里梁顶也挂着成串成排的红薯条,像在炫耀自家孩子的能耐。
苹果片儿经半月的日头暴晒,失去了水分,颜色变得深黄、淡红、咖啡色。拿一片放嘴里嚼一嚼,特别的筋道,苹果的甜香完全浓缩在苹果干里,可以用袋子装起来,慢慢品尝了。而那些阴干的红薯条,要一直等到寒冷的冬季,特别是下了大雪以后,才真正成型。它很韧、很硬,要使劲地嚼一会儿才嚼碎,这时才能品尝出红薯的异样甘甜,咽下肚,忍不住去啃第二口。
这些完全出自我们农场土孩子的手,从田野果园里捡回来的、不起眼的果实,经过认真的清洗、晾晒,自制出来的苹果干、红薯条,就成为每家每户孩子们都十分喜爱的、最家常的零食。平日里,孩子们兜里装着的,书包里塞着的,床头挂着的,不外乎这两种“土零食”。家里吃,学校里吃,看电影、听戏也吃,你吃我的、我尝他的,品尝不完的香甜。大人们也喜欢闲暇时、有客人来时、去串门聊天时,盛出一大盘红薯干,或者是用苹果干泡一壶浓色、浓味的苹果茶,边吃、边喝、边聊,有滋有味。
那个年代,这两样“变废为宝”捡拾回来、粗略加工后的苹果干、红薯条,被我们这些农场的土孩子当作了最常见、最不可少的“土零食”。收获、制作了一年又一年,家家都有,户户都吃。可是,老老少少却总觉得吃不够、吃不烦,一辈子都惦记着苹果干、红薯条浓缩的香甜。
又到深秋,再次回忆当年我们那群土孩子制作的“土零食”,仍然会口舌生津。其实,一方面是那时候物质确实匮乏,孩子们吃不到更多的食品。另一方面是这些农场果园里生长的果实,经过我们这些土孩子自己用辛勤的汗水、亲手加工出苹果干、红薯条,吃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滋味和感受,可以回味至今,可以深刻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周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