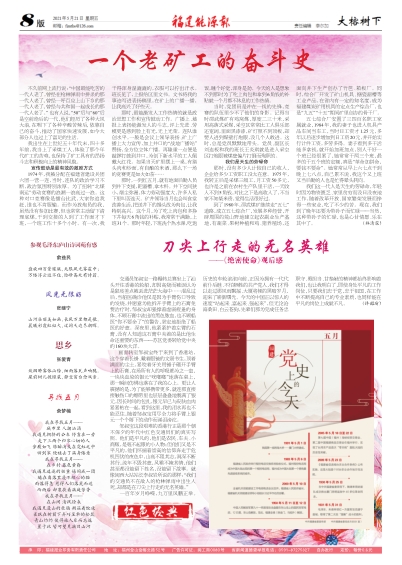发布日期:
一个老矿工的奋斗史
文章字数:1,621
不久前网上流行说:中国最能吃苦的一代人老了,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拼杀的那一代人老了,曾经一呼百应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老了,曾经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那一代人老了。”也有人说,“50”后与“60”后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他们经历了各种大风大浪,在咽下了各种辛酸苦辣后,依靠自己的奋斗,推动了国家快速发展,如今大部分人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四十多年前,我当上了采煤工人,体验了那个年代矿工的苦难,也保持了矿工具有的昂扬斗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宣传鼓动是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1974年,我被分配在福建省建设兵团六团一营一连,当时,连队的政治学习不断,政治氛围特别浓厚。为了扭转“北煤南运”劳动竞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对口竞赛像是擂台比武,大家你追我赶,谁也不肯服输。而作为放炮员的我,虽然没有参加比赛,但也常常主动留下清理底煤,干到交接的人到了工作面才下班,一个班工作十多个小时。有一次,我干得浑身湿漉漉的,衣服可以拧出汗水。班长见了,上报给区里文书。文书将我的事迹写进表扬稿里,在矿上的广播一播,让我高兴了好些天。
那时,最能激发人工作热情的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广播上、墙报上表扬能激发人的斗志,评上先进、劳模更是感到脸上有光,无上光荣。连队谁创水平,一般是会议上领导表扬、矿上广播上大力宣传,加上井口的“战地广播站”赞扬,全方位立体广播。再隆重一点便是敲锣打鼓到井口,为创下新水平的工人佩戴大红花。如果当天矿里摆上一桌,有猪头肉和炒面,有自酿的米酒,那么下一场的竞赛更是如火如荼……
那时,一到红五月,就有地面后勤人员到井下支援,耙溜槽、拿木料。井下空间狭小,烟尘弥漫,体力劳动强度大,许多人私下里叫苦连天。矿井领导当月也会叫食堂改善生活,把送井下的馒头改为肉包,让我特别高兴。这个月,为了吃上肉包和多挣下井每天6角钱的补贴,我常常干满勤,上班31个。那时年轻,下班洗个热水澡,吃饱饭,睡个好觉,浑身是劲。今天的人是想象不到那时为了吃上肉包和拿到6角钱的补贴就一个月都不休息的工作热情。
当时,党团员是冲在一线的先锋,竞赛的队伍里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记得当时邵武煤矿有鸡窝煤,厚度二三十米,采用高落式采煤,采空区常常比工人俱乐部还宽阔,里面黑漆漆,矿灯照不到顶板,却要人进到煤壁打炮眼,没几个人敢进。这时,总是党员默默地带头。党员、副区长刘连板和我的班长王炎琪就是进入采空区打炮眼被煤壁偏片打倒而殉职的。
我们是天生的劳碌命
那时,没有多少人计较自己的收入,企业给多少工资职工没太在意。1975年,我转正后是采煤三级工,月工资50多元,也许是之前在农村生产队里干活,一天收入不到5角钱,对比之下是高收入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觉得生活很好过。
到了1980年,邵武煤矿继续走“五七”道路,成立五七综合厂,发展多种经营,开辟周围的荒山野地建立起农副业生产基地,有蔬菜、果树种植和鸡、猪养殖场,还面向井下生产创办了竹笆、箱板厂。同时,综合厂开发了矿山机具、搪瓷溜槽等工业产品,在省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成为福建煤炭矿用机具的定点生产综合厂,也是“九五”“十五”期间矿里创办的骨干厂。
五七综合厂安置了三四百名职工家属就业,1984年,我的妻子也进入机具产品车间当车工,当时日工资才1.25元,多年以后逐步增加到日工资20元,并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妻子看到多干活能多拿钱,就开始加班加点,别人干好一个班已经很累了,她常常干两三个班,最多的干五个班的定额,真是“革命加拼命,要钱不要命”。她常常从早上六七点干到晚上七八点,自己累不说,我这个又上班又当后勤的人也是忙得晕头转向。
我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劳碌命,年轻时因为物资匮乏、家里贫穷而没日没夜地工作,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繁荣发展而挣得一些家业,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我们到了晚年还要为带孙子而忙碌——当然,这种带孙子的忙碌,也是心甘情愿、乐在其中了。(林清霖)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四十多年前,我当上了采煤工人,体验了那个年代矿工的苦难,也保持了矿工具有的昂扬斗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宣传鼓动是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1974年,我被分配在福建省建设兵团六团一营一连,当时,连队的政治学习不断,政治氛围特别浓厚。为了扭转“北煤南运”劳动竞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对口竞赛像是擂台比武,大家你追我赶,谁也不肯服输。而作为放炮员的我,虽然没有参加比赛,但也常常主动留下清理底煤,干到交接的人到了工作面才下班,一个班工作十多个小时。有一次,我干得浑身湿漉漉的,衣服可以拧出汗水。班长见了,上报给区里文书。文书将我的事迹写进表扬稿里,在矿上的广播一播,让我高兴了好些天。
那时,最能激发人工作热情的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广播上、墙报上表扬能激发人的斗志,评上先进、劳模更是感到脸上有光,无上光荣。连队谁创水平,一般是会议上领导表扬、矿上广播上大力宣传,加上井口的“战地广播站”赞扬,全方位立体广播。再隆重一点便是敲锣打鼓到井口,为创下新水平的工人佩戴大红花。如果当天矿里摆上一桌,有猪头肉和炒面,有自酿的米酒,那么下一场的竞赛更是如火如荼……
那时,一到红五月,就有地面后勤人员到井下支援,耙溜槽、拿木料。井下空间狭小,烟尘弥漫,体力劳动强度大,许多人私下里叫苦连天。矿井领导当月也会叫食堂改善生活,把送井下的馒头改为肉包,让我特别高兴。这个月,为了吃上肉包和多挣下井每天6角钱的补贴,我常常干满勤,上班31个。那时年轻,下班洗个热水澡,吃饱饭,睡个好觉,浑身是劲。今天的人是想象不到那时为了吃上肉包和拿到6角钱的补贴就一个月都不休息的工作热情。
当时,党团员是冲在一线的先锋,竞赛的队伍里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记得当时邵武煤矿有鸡窝煤,厚度二三十米,采用高落式采煤,采空区常常比工人俱乐部还宽阔,里面黑漆漆,矿灯照不到顶板,却要人进到煤壁打炮眼,没几个人敢进。这时,总是党员默默地带头。党员、副区长刘连板和我的班长王炎琪就是进入采空区打炮眼被煤壁偏片打倒而殉职的。
我们是天生的劳碌命
那时,没有多少人计较自己的收入,企业给多少工资职工没太在意。1975年,我转正后是采煤三级工,月工资50多元,也许是之前在农村生产队里干活,一天收入不到5角钱,对比之下是高收入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觉得生活很好过。
到了1980年,邵武煤矿继续走“五七”道路,成立五七综合厂,发展多种经营,开辟周围的荒山野地建立起农副业生产基地,有蔬菜、果树种植和鸡、猪养殖场,还面向井下生产创办了竹笆、箱板厂。同时,综合厂开发了矿山机具、搪瓷溜槽等工业产品,在省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成为福建煤炭矿用机具的定点生产综合厂,也是“九五”“十五”期间矿里创办的骨干厂。
五七综合厂安置了三四百名职工家属就业,1984年,我的妻子也进入机具产品车间当车工,当时日工资才1.25元,多年以后逐步增加到日工资20元,并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妻子看到多干活能多拿钱,就开始加班加点,别人干好一个班已经很累了,她常常干两三个班,最多的干五个班的定额,真是“革命加拼命,要钱不要命”。她常常从早上六七点干到晚上七八点,自己累不说,我这个又上班又当后勤的人也是忙得晕头转向。
我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劳碌命,年轻时因为物资匮乏、家里贫穷而没日没夜地工作,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繁荣发展而挣得一些家业,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我们到了晚年还要为带孙子而忙碌——当然,这种带孙子的忙碌,也是心甘情愿、乐在其中了。(林清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