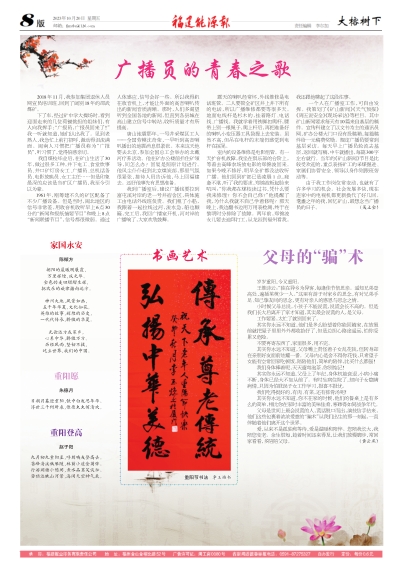发布日期:
广播员的青春之歌
文章字数:1,326
2018年11月,我参加集团退休人员网宣员培训班,回到了阔别18年的邵武煤矿。
下了车,经过矿中学大操场时,看到迎面走来的几位荷锄挑担的姐妹们,有人向我挥手:“广报员,广报员回来了!”我一听就知道,她们认出我了。见到老熟人,我急忙上前打招呼,激动得泪流满面。闽南人习惯把广播员称为“广报员”,听习惯了,觉得倍感亲切。
我自煤校毕业后,在矿山生活了30年,做过很多工种,井下电工、食堂炊事员、井口矿灯房女工、广播员、总机话务员、电影放映员、女工主任……但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当矿区广播员,我至今引以为豪。
1961年,刚筹建不久的矿区配备了不少广播设备。但是当时,闽北地区的信号非常差,用收音机收听早上6点30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晚上8点“新闻联播节目”,信号都很微弱。通过人体感应,信号会好一些。所以我得趴在收音机上,才能让外面的高音喇叭传出的新闻音质清晰。那时,人们多渴望听到全国各地的新闻,但直到各县城在高山建立信号中转站,收听质量才有所提高。
唐山地震那年,一号井采煤区工人——全国劳模沈奇荣,一早听到高音喇叭播出的地震消息很紧张。本来这天他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北戴河疗养活动。他在矿办公楼前拦住矿领导,问怎么办?回复是照原计划进行。他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煤炭部,那里气氛很紧张,接待人员告诉他,马上回福建去。还好他事先有思想准备。
我到广播室后,建议广播线要拉到富屯溪对岸的老一号井宿舍区,具体施工由电话外线班负责。我们租了小船,我跟着一起拉线过河,流水急,船也颠簸,完工后,我回广播室开机,河对岸的广播响了,大家欢欣鼓舞。
露天的喇叭经常坏,外线维修是电话班管。二人要管全矿区井上井下所有的电话,所以广播维修都要等很多天。地面电线杆是杉木的,挂着路灯、电话线、广播线。我就学着用铁脚扣爬杆,腰带上别一根绳子,爬上杆后,再把准备好的喇叭小变压器工具袋提上去安装。虽然不高,但吊在电杆的末端仍感觉到电杆在摇晃。
室内的设备维修是电影组管。有一天扩音机故障,我坐在俱乐部的台阶上,等着去高峰农场放电影的郑锦波回来。如果今晚不修好,明早全矿都没法收听广播。他们回到矿部已是凌晨1点,疲惫不堪,听了我的要求,郑锦波板起脸来吼叫:“你我都在煤校读过书,凭什么要我来修理?你不会自己修?”他提醒了我,为什么我就不自己学着修呢?那天晚上,我边翻书边用万用表检测,终于在黎明时分排除了故障。两年前,郑锦波女儿要去迪拜打工,从龙岩到福州看我,我还跟他聊起了这段往事。
一个人在广播室工作,可自由发挥。我策划了《矿山新闻》《天气预报》《周五说安全》《现场采访》等栏目。其中矿山新闻要求每天有10篇来自基层的稿件。宣传科建立了以文书为主的通讯员网,矿办公楼大门口设有投稿箱,每篇稿件给一元稿费奖励。规定广播员要常到基层采访。每天早上广播员轮流去基层,返回就写稿,中午就播出,每篇300字左右就行。当年的《矿山新闻》节目是比较受欢迎的,重点表扬矿工的采煤掘进、家属们协管安全、领导以身作则跟班劳动等。
由于我工作岗位常变动,也就有了许多学习的机会。社会发展多快,现在连家中的电视机都更新换代了好几回。耄耋之年的我,回忆矿山,最想念当广播员的日子。(吴土金)
下了车,经过矿中学大操场时,看到迎面走来的几位荷锄挑担的姐妹们,有人向我挥手:“广报员,广报员回来了!”我一听就知道,她们认出我了。见到老熟人,我急忙上前打招呼,激动得泪流满面。闽南人习惯把广播员称为“广报员”,听习惯了,觉得倍感亲切。
我自煤校毕业后,在矿山生活了30年,做过很多工种,井下电工、食堂炊事员、井口矿灯房女工、广播员、总机话务员、电影放映员、女工主任……但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当矿区广播员,我至今引以为豪。
1961年,刚筹建不久的矿区配备了不少广播设备。但是当时,闽北地区的信号非常差,用收音机收听早上6点30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晚上8点“新闻联播节目”,信号都很微弱。通过人体感应,信号会好一些。所以我得趴在收音机上,才能让外面的高音喇叭传出的新闻音质清晰。那时,人们多渴望听到全国各地的新闻,但直到各县城在高山建立信号中转站,收听质量才有所提高。
唐山地震那年,一号井采煤区工人——全国劳模沈奇荣,一早听到高音喇叭播出的地震消息很紧张。本来这天他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北戴河疗养活动。他在矿办公楼前拦住矿领导,问怎么办?回复是照原计划进行。他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煤炭部,那里气氛很紧张,接待人员告诉他,马上回福建去。还好他事先有思想准备。
我到广播室后,建议广播线要拉到富屯溪对岸的老一号井宿舍区,具体施工由电话外线班负责。我们租了小船,我跟着一起拉线过河,流水急,船也颠簸,完工后,我回广播室开机,河对岸的广播响了,大家欢欣鼓舞。
露天的喇叭经常坏,外线维修是电话班管。二人要管全矿区井上井下所有的电话,所以广播维修都要等很多天。地面电线杆是杉木的,挂着路灯、电话线、广播线。我就学着用铁脚扣爬杆,腰带上别一根绳子,爬上杆后,再把准备好的喇叭小变压器工具袋提上去安装。虽然不高,但吊在电杆的末端仍感觉到电杆在摇晃。
室内的设备维修是电影组管。有一天扩音机故障,我坐在俱乐部的台阶上,等着去高峰农场放电影的郑锦波回来。如果今晚不修好,明早全矿都没法收听广播。他们回到矿部已是凌晨1点,疲惫不堪,听了我的要求,郑锦波板起脸来吼叫:“你我都在煤校读过书,凭什么要我来修理?你不会自己修?”他提醒了我,为什么我就不自己学着修呢?那天晚上,我边翻书边用万用表检测,终于在黎明时分排除了故障。两年前,郑锦波女儿要去迪拜打工,从龙岩到福州看我,我还跟他聊起了这段往事。
一个人在广播室工作,可自由发挥。我策划了《矿山新闻》《天气预报》《周五说安全》《现场采访》等栏目。其中矿山新闻要求每天有10篇来自基层的稿件。宣传科建立了以文书为主的通讯员网,矿办公楼大门口设有投稿箱,每篇稿件给一元稿费奖励。规定广播员要常到基层采访。每天早上广播员轮流去基层,返回就写稿,中午就播出,每篇300字左右就行。当年的《矿山新闻》节目是比较受欢迎的,重点表扬矿工的采煤掘进、家属们协管安全、领导以身作则跟班劳动等。
由于我工作岗位常变动,也就有了许多学习的机会。社会发展多快,现在连家中的电视机都更新换代了好几回。耄耋之年的我,回忆矿山,最想念当广播员的日子。(吴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