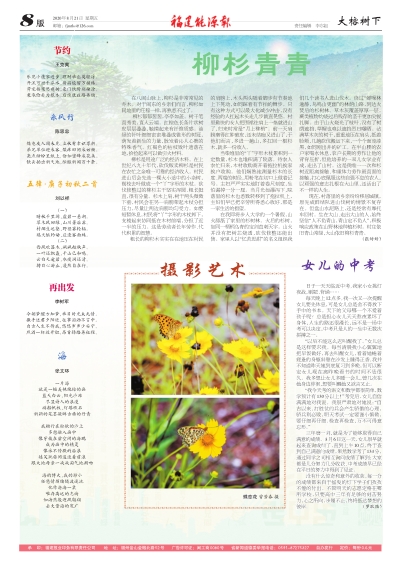发布日期:
柳杉青青
文章字数:1,161
在八闽山脉上,柳杉是非常常见的乔木。对于闽东的乡亲们而言,柳杉如同地里的庄稼一样,再熟悉不过了。
柳杉郁郁葱葱,亭亭如盖。树干笔直秀美,直入云端。红棕色长条片状树皮层层叠叠,触摸起来有纤维质感。油绿的针叶细细密密堆叠成锥形的树冠,萌发着新生的力量,散发着沁人心脾的特殊香气。红褐色的枯枝败叶遗落在地,拾捡起来可以做引火材料。
柳杉是用途广泛的经济木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砍伐贩卖柳杉是村民在农忙之余唯一可靠的经济收入。村民进山后会先选一棵大小适中的小杂树,削枝去叶做成一个“丫”字形的木杖。砍伐修整过的柳杉主干坚实浑圆、粗长挺直,很有分量。杉木上肩,树干两头微微下垂,村民会在另一肩膀架起木杖分担压力,尽量让两边肩膀均匀受力。如要短暂休息,村民将“丫”字形的木杖卸下,支棱起来协同抵在木材前端,分担了近一半的压力。这是劳动者长年劳作、代代积累的智慧。
粗长的柳杉木实实在在地压在村民的肩膀上,木头两头随着脚步有节奏地上下晃动,如同踩着有节拍的舞步。只有这种方式可以最大化减少冲击,没有经验的人扛起木头走几步就直晃悠。村里勤快的女人把围裙往肩上一垫就进山了,归来时常是“月上柳梢”。前一天肩膀磨得红肿破皮,还未结痂又进山了,于他们而言,多进一趟山,多扛回一根杉木,就多一份收入。
当柴堆里的“丫”字形木杖累积到一定数量,杉木也堆积满了院落。待农人农忙归来,木材收购商开着拖拉机挨家挨户收购。他们娴熟地测量杉木的长度、两端的树径,用粉笔在切口上做着记号。主妇严严实实地盯着卷尺刻度,生怕漏掉一分一厘。当月光如瀑泻下,院落里的杉木也悉数转移到了拖拉机上,主妇们早已把辛劳所得悉心收好,那是一家生活的指望。
在我即将步入大学的一个暑假,山火舔舐了家里的杉树林。火后的杉树,如同一柄柄乌青的宝剑直刺天宇。山火并没有把树芯烧透,砍伐修整还能出售。家里人以“忆苦思甜”的名义组织我们几个读书人进山伐木。绕过“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林荫山路,到达火焚后的杉树林。草木灰覆盖厚厚一层,蕨类植物灼烧过后残存的茎干更加尖锐扎脚。由于山火烧光了枝叶,没有了树荫遮挡,草帽也难以遮挡烈日曝晒。沾满草木灰的树干,重重地压在肩头,抵着脸颊,几趟砍伐搬运下来,一个个面庞漆黑,如同刚出井的矿工。在半山腰的农户家喝水休息,农户长期的劳作让他的背脊压折,但他培养的一双儿女学业有成,走出了山村。这是我唯一一次和杉树近距离接触、和重体力劳作最直面的接触,打心底佩服这些自强不息的农人,以顽强的意志扎根在大山里,还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现在,村落里的乡亲纷纷移居城镇,原先成群结队进山伐树的情景不复存在。但盘山水泥路上,还是经常有摩托车回村。生在大山、走出大山的人,始终坚信“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积极响应政策在山野林地种植杉树。村庄依旧青山常绿,大山依旧柳杉青青。
(张婷婷)
柳杉郁郁葱葱,亭亭如盖。树干笔直秀美,直入云端。红棕色长条片状树皮层层叠叠,触摸起来有纤维质感。油绿的针叶细细密密堆叠成锥形的树冠,萌发着新生的力量,散发着沁人心脾的特殊香气。红褐色的枯枝败叶遗落在地,拾捡起来可以做引火材料。
柳杉是用途广泛的经济木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砍伐贩卖柳杉是村民在农忙之余唯一可靠的经济收入。村民进山后会先选一棵大小适中的小杂树,削枝去叶做成一个“丫”字形的木杖。砍伐修整过的柳杉主干坚实浑圆、粗长挺直,很有分量。杉木上肩,树干两头微微下垂,村民会在另一肩膀架起木杖分担压力,尽量让两边肩膀均匀受力。如要短暂休息,村民将“丫”字形的木杖卸下,支棱起来协同抵在木材前端,分担了近一半的压力。这是劳动者长年劳作、代代积累的智慧。
粗长的柳杉木实实在在地压在村民的肩膀上,木头两头随着脚步有节奏地上下晃动,如同踩着有节拍的舞步。只有这种方式可以最大化减少冲击,没有经验的人扛起木头走几步就直晃悠。村里勤快的女人把围裙往肩上一垫就进山了,归来时常是“月上柳梢”。前一天肩膀磨得红肿破皮,还未结痂又进山了,于他们而言,多进一趟山,多扛回一根杉木,就多一份收入。
当柴堆里的“丫”字形木杖累积到一定数量,杉木也堆积满了院落。待农人农忙归来,木材收购商开着拖拉机挨家挨户收购。他们娴熟地测量杉木的长度、两端的树径,用粉笔在切口上做着记号。主妇严严实实地盯着卷尺刻度,生怕漏掉一分一厘。当月光如瀑泻下,院落里的杉木也悉数转移到了拖拉机上,主妇们早已把辛劳所得悉心收好,那是一家生活的指望。
在我即将步入大学的一个暑假,山火舔舐了家里的杉树林。火后的杉树,如同一柄柄乌青的宝剑直刺天宇。山火并没有把树芯烧透,砍伐修整还能出售。家里人以“忆苦思甜”的名义组织我们几个读书人进山伐木。绕过“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林荫山路,到达火焚后的杉树林。草木灰覆盖厚厚一层,蕨类植物灼烧过后残存的茎干更加尖锐扎脚。由于山火烧光了枝叶,没有了树荫遮挡,草帽也难以遮挡烈日曝晒。沾满草木灰的树干,重重地压在肩头,抵着脸颊,几趟砍伐搬运下来,一个个面庞漆黑,如同刚出井的矿工。在半山腰的农户家喝水休息,农户长期的劳作让他的背脊压折,但他培养的一双儿女学业有成,走出了山村。这是我唯一一次和杉树近距离接触、和重体力劳作最直面的接触,打心底佩服这些自强不息的农人,以顽强的意志扎根在大山里,还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现在,村落里的乡亲纷纷移居城镇,原先成群结队进山伐树的情景不复存在。但盘山水泥路上,还是经常有摩托车回村。生在大山、走出大山的人,始终坚信“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积极响应政策在山野林地种植杉树。村庄依旧青山常绿,大山依旧柳杉青青。
(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