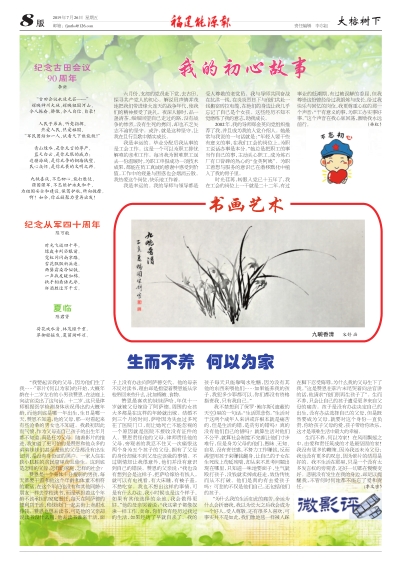发布日期:
生而不养何以为家
文章字数:1,498
“我要起诉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了我……”影片《何以为家》的开始,大概年龄在十二岁左右的小男孩赞恩,在法庭上向法官说出了这句话。十二岁,这只是律师根据医学检测身体状况得出的大概年龄,而他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生日是哪一天,赞恩不知道,他的父母,那一对看起来有些沧桑的男女也不知道。我最初因此而气愤,作为父母连自己孩子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真是枉为父母。随着影片的推进,我知道了更可怕的是赞恩和他众多的弟弟妹妹们甚至是他的父母都没有出生证明,是没有身份证的黑户。一家人住在狭小肮脏的贫民窟里苟且偷生。这到底是怎样的父母,怎样的家庭,怎样的社会?
赞恩是一个身体十分瘦弱的男孩,每天都要干着和他这个年龄和体重不相符的重活,在这个年纪他没有和其他同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读书,而是承担着这个年龄不该承担的家庭重任,每天在阿萨德的便利店干活,和妹妹们一起去街上卖甜水挣钱。赞恩也想去读书,可是他的父亲却说读书没什么用,他去读书谁来干活,面子上没有办法向阿萨德交代。他的母亲不反对读书,理由却是指望着赞恩能从学校带回来些什么,比如棉被、食物。
赞恩最喜欢的妹妹萨哈,年仅十一岁就被父母嫁给了阿萨德,周围的女孩大多都是在这样的年龄就出嫁。结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萨哈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医院门口,而让她死亡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医院不接收没有证件的人。赞恩责怪他的父母,律师责怪他的父母,旁观者的我忍不住又一次痛恨这两个身为五个孩子的父母,拥有了父母的身份却做不到父母应该做的事情。不过剧情却让我很意外,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赞恩的父亲说:“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把萨哈嫁给有钱人,就可以有电视看,有大床睡,有被子盖,不愁吃穿。我也不想出这样的事情,可是有什么办法,我小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我会做得更好。”他的母亲哭着说:我这辈子都像奴隶一样工作、卖命,你们没有经历过我过的生活,如果经历了早就自杀了。我的孩子每天只能靠喝水吃糖,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来喂他们……如果能养我的孩子,我犯多少罪都可以,你们都没有资格指责我,只有我自己。
我不禁想到了保罗·鲍尔斯《遮蔽的天空》里的一句话:生活即悲伤。生活对于这两个成年人来讲或许根本就是痛苦的,但是生活的错,是贫穷的错吗?真的没有他们自己的错吗?就算生活对他们不公平,就算社会制度不完善让他们寸步难行,但是身为父母的他们,愚昧、无知、自私、没有责任感,不努力工作赚钱,反而渴望用孩子来赚钱翻身,让自己的子女在生死线上苟延残喘,却从来不思考问题出现在哪里,只知道一味地要面子,生气就殴打孩子,没钱就卖掉或赶走,效仿传统而从不打破。他们是真的有去爱孩子吗?可悲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包括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我的生活如此的痛苦,命运为什么会折磨我,我以为长大之后我会成为一个好人,受人尊敬,还有很多人喜欢,可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像地毯一样被人踩在脚下忍受侮辱,为什么我的父母生下了我。”这是赞恩在影片末尾哭着向法官讲的话,他请求“他们别再生孩子了”。生而不养,只会让自己的孩子遭受更多来自父母的痛苦。孩子是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出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既然要成为父母,就要对这个身份一直负责,你给孩子父母的爱,孩子带给你欢乐,这才是艰难生活中最大的幸福。
生而不养,何以为家!在风雨飘摇之中,由爱和责任筑成的才是最坚固的家!我没有更多的鞭策,因为我还未为父母;我也没有更多的叹息,因为影片的结局是好的。我不生活在那里,只是一个没有太多发言权的旁观者,还好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悲剧没有发生在我的身边,却足以提醒我,不管何时何地都不能忘了爱和责任。(李文密)
赞恩是一个身体十分瘦弱的男孩,每天都要干着和他这个年龄和体重不相符的重活,在这个年纪他没有和其他同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读书,而是承担着这个年龄不该承担的家庭重任,每天在阿萨德的便利店干活,和妹妹们一起去街上卖甜水挣钱。赞恩也想去读书,可是他的父亲却说读书没什么用,他去读书谁来干活,面子上没有办法向阿萨德交代。他的母亲不反对读书,理由却是指望着赞恩能从学校带回来些什么,比如棉被、食物。
赞恩最喜欢的妹妹萨哈,年仅十一岁就被父母嫁给了阿萨德,周围的女孩大多都是在这样的年龄就出嫁。结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萨哈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医院门口,而让她死亡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医院不接收没有证件的人。赞恩责怪他的父母,律师责怪他的父母,旁观者的我忍不住又一次痛恨这两个身为五个孩子的父母,拥有了父母的身份却做不到父母应该做的事情。不过剧情却让我很意外,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赞恩的父亲说:“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把萨哈嫁给有钱人,就可以有电视看,有大床睡,有被子盖,不愁吃穿。我也不想出这样的事情,可是有什么办法,我小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我会做得更好。”他的母亲哭着说:我这辈子都像奴隶一样工作、卖命,你们没有经历过我过的生活,如果经历了早就自杀了。我的孩子每天只能靠喝水吃糖,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来喂他们……如果能养我的孩子,我犯多少罪都可以,你们都没有资格指责我,只有我自己。
我不禁想到了保罗·鲍尔斯《遮蔽的天空》里的一句话:生活即悲伤。生活对于这两个成年人来讲或许根本就是痛苦的,但是生活的错,是贫穷的错吗?真的没有他们自己的错吗?就算生活对他们不公平,就算社会制度不完善让他们寸步难行,但是身为父母的他们,愚昧、无知、自私、没有责任感,不努力工作赚钱,反而渴望用孩子来赚钱翻身,让自己的子女在生死线上苟延残喘,却从来不思考问题出现在哪里,只知道一味地要面子,生气就殴打孩子,没钱就卖掉或赶走,效仿传统而从不打破。他们是真的有去爱孩子吗?可悲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包括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我的生活如此的痛苦,命运为什么会折磨我,我以为长大之后我会成为一个好人,受人尊敬,还有很多人喜欢,可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像地毯一样被人踩在脚下忍受侮辱,为什么我的父母生下了我。”这是赞恩在影片末尾哭着向法官讲的话,他请求“他们别再生孩子了”。生而不养,只会让自己的孩子遭受更多来自父母的痛苦。孩子是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出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既然要成为父母,就要对这个身份一直负责,你给孩子父母的爱,孩子带给你欢乐,这才是艰难生活中最大的幸福。
生而不养,何以为家!在风雨飘摇之中,由爱和责任筑成的才是最坚固的家!我没有更多的鞭策,因为我还未为父母;我也没有更多的叹息,因为影片的结局是好的。我不生活在那里,只是一个没有太多发言权的旁观者,还好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悲剧没有发生在我的身边,却足以提醒我,不管何时何地都不能忘了爱和责任。(李文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