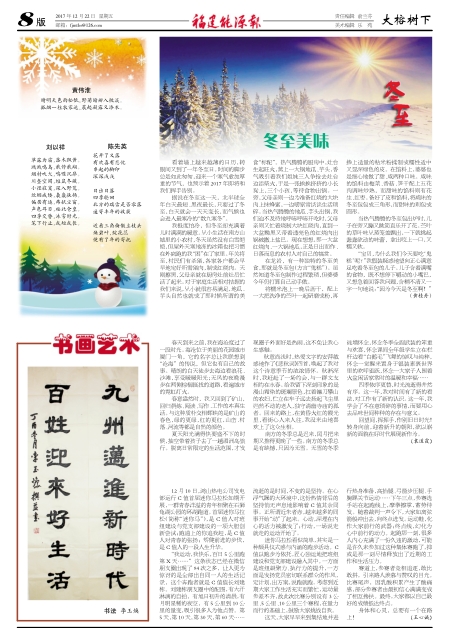发布日期:
冬至美味
文章字数:889
看着墙上越来越薄的日历,转眼间又到了一年冬至日。时间的脚步总是如此匆匆,迎来一个寒气愈加厚重的节气,也预示着2017年即将和我们挥手告别。
据说在冬至这一天,北半球全年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只要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而气候也会进入最寒冷的“数九寒冬”。
我极度怕冷,但冬至却充满着儿时满满的暖意。从小生活在南方山城里的小农村,冬天虽然没有白雪皑皑,但屋外天寒地冻的冰霜也把习惯在外疯跑的我“困”在了家里。年关将至,村民们有杀猪,各家各户都会早早地定好所需猪肉,制成红烧肉。天刚擦黑,父母亲就在厨房灶前灶后忙活了起来。对于家庭生活相对拮据的我们来说,从小就很容易满足,地瓜、芋头自然也就成了那时候所谓的美食“标配”。热气腾腾的厨房中,灶台生起旺火,蒸上一大锅地瓜、芋头,香气吸引着我们姐妹三人争抢去灶台边添柴火,于是一张挨挨挤挤的小长凳上,三个小孩,等待食物出锅。一旁,父母亲则一边为准备红烧的大块肉上抹蜂蜜,一边唠家常谈谈生活琐碎。当热气腾腾的地瓜、芋头出锅,我们迫不及待地呼哧呼哧开吃时,父母亲则又忙着烧制大块红烧肉,直到一大盆黝黑又带着透亮色的红烧肉出锅被撒上盐巴。现在想想,那一大盆红烧肉、一大锅地瓜,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人对自己的犒赏。
在龙岩,有一种独特的冬至美食,那就是冬至包(方言“鬼糕”)。虽然知道冬至包制作过程繁琐,但婆婆今年仍打算自己动手做。
将糯米泡上一晚后沥干,配上一大把洗净的苎叶一起研磨成粉,再掺上适量的粘米粉揉制成糯性适中又显深绿色的皮。在馅料上,婆婆也是细心地做了甜、咸两种口味。咸味的馅料由梅菜、香菇、笋干配上五花肉调味炒熟,而甜味的馅料则有花生、红枣。备好了皮和馅料,将咸味的冬至包包成三角形,而甜味的则包成圆形。
当热气腾腾的冬至包出炉时,儿子在旁又蹦又跳简直乐开了花。苎叶的草叶味从蒸笼盖飘出,一下就挑起蠢蠢欲动的味蕾,拿出咬上一口,又糯又软。
“宝贝,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吃‘鬼糕’呢?”我假装疑惑地望向正心满意足吃着冬至包的儿子。儿子含着满嘴的食物,既不想停下嚼动的小嘴巴,又想急着回答我问题,含糊不清又一字一句地说:“因为今天是冬至啊!”
(黄桂丹)
据说在冬至这一天,北半球全年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只要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而气候也会进入最寒冷的“数九寒冬”。
我极度怕冷,但冬至却充满着儿时满满的暖意。从小生活在南方山城里的小农村,冬天虽然没有白雪皑皑,但屋外天寒地冻的冰霜也把习惯在外疯跑的我“困”在了家里。年关将至,村民们有杀猪,各家各户都会早早地定好所需猪肉,制成红烧肉。天刚擦黑,父母亲就在厨房灶前灶后忙活了起来。对于家庭生活相对拮据的我们来说,从小就很容易满足,地瓜、芋头自然也就成了那时候所谓的美食“标配”。热气腾腾的厨房中,灶台生起旺火,蒸上一大锅地瓜、芋头,香气吸引着我们姐妹三人争抢去灶台边添柴火,于是一张挨挨挤挤的小长凳上,三个小孩,等待食物出锅。一旁,父母亲则一边为准备红烧的大块肉上抹蜂蜜,一边唠家常谈谈生活琐碎。当热气腾腾的地瓜、芋头出锅,我们迫不及待地呼哧呼哧开吃时,父母亲则又忙着烧制大块红烧肉,直到一大盆黝黑又带着透亮色的红烧肉出锅被撒上盐巴。现在想想,那一大盆红烧肉、一大锅地瓜,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人对自己的犒赏。
在龙岩,有一种独特的冬至美食,那就是冬至包(方言“鬼糕”)。虽然知道冬至包制作过程繁琐,但婆婆今年仍打算自己动手做。
将糯米泡上一晚后沥干,配上一大把洗净的苎叶一起研磨成粉,再掺上适量的粘米粉揉制成糯性适中又显深绿色的皮。在馅料上,婆婆也是细心地做了甜、咸两种口味。咸味的馅料由梅菜、香菇、笋干配上五花肉调味炒熟,而甜味的馅料则有花生、红枣。备好了皮和馅料,将咸味的冬至包包成三角形,而甜味的则包成圆形。
当热气腾腾的冬至包出炉时,儿子在旁又蹦又跳简直乐开了花。苎叶的草叶味从蒸笼盖飘出,一下就挑起蠢蠢欲动的味蕾,拿出咬上一口,又糯又软。
“宝贝,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吃‘鬼糕’呢?”我假装疑惑地望向正心满意足吃着冬至包的儿子。儿子含着满嘴的食物,既不想停下嚼动的小嘴巴,又想急着回答我问题,含糊不清又一字一句地说:“因为今天是冬至啊!”
(黄桂丹)